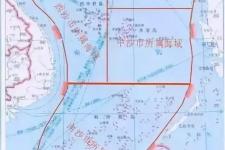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28期,原文标题《末日快乐》
如果真的要寻找纯粹的仁慈,或者彻底的邪恶,还得从人类的头脑中去找,而且很可能你会在同一个人的头脑里找到。
主笔/陈赛

尼尔·盖曼(法新社 供图)
好兆头
这是一个关于世界末日的搞笑故事:撒旦之子的诞生,宣告了世界末日的到来。天堂和地狱都摩拳擦掌,打算大战一场,唯有一个天使和一个恶魔因为在人间待久了,沾染了人间的习气,觉得世界毁了挺可惜的,于是决定携手阻止末日的到来。
《好兆头》的原著写于30年前。两位作者,尼尔·盖曼和特里·普拉切特,在当时英国文坛还籍籍无名,如今都已经名满天下。盖曼是新一代幻想文学的代表人物,而普拉切特则被认为是“当代托尔金”。
在这本书的后记里,他们都谈到了彼此之间类似于一见钟情的惺惺相惜。尼尔·盖曼擅长写神话和恐怖,各种神话元素信手拈来,随意戏仿和恶搞,他最著名的小说《美国众神》是讲新神上位,旧神下岗,以新旧神仙大战来讲美国的历史和价值观的激烈冲突;普拉切特则擅长奇幻和冷幽默,他在《碟形世界》构建的平行世界是这样的——广漠的太空之中,一个超级大海龟背上站着四头大象,大象的背上驮着一个奇异的圆形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写童话,写硬派侦探故事、吸血鬼政治喜剧,内核却是关于人类的善与恶,罪与罚、性与死亡、爱与偏执,以及种族主义、宗教仇恨、战争等等。
在写了27本奇幻小说之后,普拉切特在59岁那年被诊断出患有一种罕见的早期阿尔茨海默病,并于7年后去世。去世之前,他请求盖曼独自将《好兆头》拍成电视剧。
其实,在普拉切特生前,他们曾经多次想过把这本小说拍成电影,而且约定,要么两人一起拍,要么干脆不拍。他们还设想过一起出现在电影里某个寿司店的背景里,客串一对食客。这个愿望当然没有实现,但如果你仔细看天使亚茨拉斐尔的旧书店,那里挂着普拉切特著名的黑色软呢帽和围巾。
参加完普拉切特的葬礼,盖曼开始写《好兆头》的第一集电视剧本。世界刚刚被创造出来,一个天使一个恶魔,一白一黑,站在伊甸园高高的城墙之上,目送亚当和夏娃离开伊甸园。他们一个是邪恶的诱惑者,诱惑人类之祖吃下了智慧树上的苹果;另一个是热心过头的保护者,不仅偷偷送走他们,还把自己的炎剑送给了他们。但有一瞬间,天使担心自己是不是干了坏事,而恶魔则怀疑自己恐怕做了一件好事。这时,人间第一场雨落下来了,天使张开翅膀,遮住了恶魔的身体,一个异常甜蜜而又惆怅的瞬间。
天使与恶魔
在第三集,盖曼用了史上最长的片头,介绍了天使亚茨拉斐尔与恶魔克鲁利六千年的友谊。他们共同经历了伊甸园苹果事件,诺亚方舟,耶稣受难,在古罗马小酒馆喝过酒,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黎吃过可丽饼,在莎士比亚的圆形剧场一起看过《哈姆雷特》,还被莎士比亚偷了几句台词。到了“二战”的伦敦,恶魔跳着脚跑进教堂,从纳粹间谍手里救他的天使朋友,可算有情有义,两肋插刀了。六千年来,他们一起兜风,一起喝酒聊天,一起在湖边散步喂鸭子,但这样的情谊始终维持着一种欲语还休的含蓄,这一点倒是非常英国的。
天使亚茨拉斐尔是典型的好孩子,天真纯良,循规蹈矩,还有三分傲娇,三分拘谨,四分呆萌。小说中说他给人三个基本印象:第一,他是英国人;第二,他很聪明;第三,他比十篇腐女同人文的主角绑在一起还基。在剧中,英国演员麦克·辛简直把这种形象演得活灵活现。
大卫·田纳德扮演的克鲁利则是典型的坏小子形象,整天戴一副墨镜,放荡不羁,愤世嫉俗,但又嘴硬心软,书中关于他的出场介绍是,“一个不能说堕落,更像是‘慢慢悠悠往下溜达的天使’”。
本来一个天使一个恶魔,应该黑白分明,正邪不两立才对。但问题是,这两位神仙都不是那么擅长自己的工作。天使不是那么好的天使,恶魔也不是那么称职的恶魔。而且,他们渐渐意识到,既然他们的上司都不怎么关心事情是如何办成的,与其各自苦哈哈的你行善我作恶搞到最后善恶相抵徒劳无功,还不如彼此合作,互相代班,浑水摸鱼,逍遥人间。至于天使何以有混蛋的潜质,而恶魔何以有善良的火花,到底是天性如此,还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就无从判断了。
总之,在人间逍遥快活几千年之后,天使和恶魔都觉得这个世界还不错。尽管并不需要,但他们都爱上了人间的美食和艺术。天使爱吃恶魔蛋(一种芥末鸡蛋),恶魔喜欢天使白蛋糕;天使喜欢舞蹈,魔鬼热爱摇滚;天使喜欢悲剧,魔鬼热爱喜剧;天使爱书成狂,魔鬼爱车如命……这一切,他们的总部和同行当然完全不能理解。
有趣的是,最坚决要拯救世界的,竟然是恶魔。表面上看,他的理由很自私,就是人间有很多好东西,毁了怪可惜的。就像他拉天使入伙时列举的,“到时候没有阿尔伯特音乐厅,没有格莱德堡歌剧院,只有天籁之音……也不会有那种你常去的美味小餐馆了,没有莳萝酱渍鲑鱼片,也没有老书店了……”
但更深一层的理由,是他一开始就看穿了天堂与地狱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如他所说,大部分恶魔并非天生邪恶,而更像是勤勤恳恳的税务监察员——也许是做着不受欢迎的工作,但对全局来说至关重要。同样,天使也并非都是道德标兵,他就遇到过两三个家伙,一遇到要对冒渎之人施以正义惩戒的任务,就表现得特别积极,下手狠得要命。“总而言之,每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只是履行职责罢了。”
所以,地狱并非邪恶的蓄水池,天堂也不是仁慈的喷泉,它们只是宇宙大棋局的两个玩家。“咱们何必讨论什么善与恶?不过是两个阵营的名字罢了。”
他认为,如果真的要寻找纯粹的仁慈,或者彻底的邪恶,还得从人类的头脑中去找,而且很可能你会在同一个人的头脑里找到。六千年来,人类在这个世界上干的事情,无论善恶,都与天堂和地狱没什么关系。事实上,他本人还为人类背了不少黑锅,比如发明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和引发“二战”。至于自拍是不是他的杰作,还有待神学家考证。
在剧里,天堂和地狱被安排在同一个大楼里,天堂在顶层,大平层,宽敞明亮、风景无敌,从装修风格看很像是某硅谷高科技大公司。地狱在地下室,阴暗嘈杂,臭气熏天,蚊蝇乱舞。虽然办公环境天差地别,但总的来说,两个地方同样的沉闷无趣。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剧几乎可以看成是一个办公室喜剧,大老板有一个莫名其妙的伟大计划,管理层一个个像是打了鸡血的白痴,而普通小职员们,无论天使还是恶魔,做了几千年的文书工作,一个个都是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
只有亚茨拉斐尔和克鲁利在人间过着一种有创造力的生活,对新技术保持着好奇心,尤其是克鲁利,当他的同事们还在遵循老一套的手艺,经年累月地对付一个灵魂,比如这里诱惑一名牧师,那里腐化一名政客,他干的事情是,把伦敦地区所有的手机网络都搞瘫痪了——1500万人怒火冲天,要把愤怒发泄在别人身上,而这些人又把火撒在另一批人身上……一根小手指头都不用动,就让“成千上万的灵魂都蒙上了薄薄一层黯淡锈色”。
可以想象,如果这本小说被拍成一部好莱坞大片,撒旦之子重组世界、亚特兰蒂斯突然浮出海面,西藏人挖的大地道,都会是视觉冲击力极强的画面,但至少在这部电视剧里,更让我们感到愉悦的是这种充满想象力的英式吐槽。
英国作家G.K.切斯特顿曾经说过,幻想小说作为一门艺术的独特之处在于,以一种陌生的方式呈现日常之物,从而让读者以新的目光来审视它们。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人们对身边事物熟视无睹,万事万物都变得模糊不清了,所以我们需要时时借助幻想,从熟悉感、贫乏感和对事物的占有感之中突围,从而获得更清晰的视野。难怪在小说的开头,盖曼和普拉切特将这本书献给了这位前辈作家。

美剧《好兆头》剧照
末日喜剧
2002年,美国导演特里·吉利安曾经想过把《好兆头》搬上大银幕,让强尼·戴普和罗宾·威廉姆斯分别饰演恶魔和天使,但因为“9·11”事件发生不久,整个世界还沉浸在世界末日的真实恐惧里,没有人有心情看一部关于世界末日的喜剧片。
今天的气氛似乎恰到好处。末日感没那么急迫,但焦虑却无处不在。气候变暖、环境污染、核战争、贸易战、人工智能……你无法指出某个具体的末日源头,但你的恐惧更加庞杂、深刻,与日常生活更紧密地交织。最令人不安的是,你隐约意识到自己就是这个庞大的末日机器的一部分。所以,当末日四骑士出现的时候,我还以为盖曼至少会为四位骑士安排几个竞争对手,比如机器人、人工病毒、社交媒体什么的。
按照《启示录》的说法,在世界终结之时,将有羔羊解开书卷的七个封印,唤来分别骑着白、红、黑、绿四匹马的骑士,将战争、饥荒、瘟疫和死亡带给接受最终审判的人类,届时天地万象失调,日月为之变色,随后便是世界的毁灭。
现代社会,科技昌明,四骑士当然不再骑马,而是开着很拉风的摩托。第一个被召唤的是战争,一个红发战地女记者,每次有战争爆发,她一定第一个到达现场。或者说,她所到之处,必然有冲突、战争爆发。比如剧中她第一次出场,就把一场好好的停战签字仪式变成了血肉横飞的枪战现场,而导火索竟然是谁先在协议上签字。在等待末日召唤的过程里,她已经这样自娱自乐了六千年。
饥荒是一个高大的黑人,一个成功商人,连锁餐厅老板,专门卖毫无营养的减肥食品,最喜欢看人们在高级餐厅里吃不饱。在他的餐厅里,服务员给一位穿着华丽的女食客上了菜,主菜是花椰菜分子冻衬鸡肉末佐蘑菇泡沫,然后冲着女食客的脸捏破了一个气泡,就算是开胃菜——“薰衣草香味空气球”。
第三位骑士是污染,一个一头白发、满身肮脏的亚洲年轻人。出场的时候,他正坐在河边的长椅上,欣赏着被白色泡沫和棕色淤泥裹挟淤滞的河道,而那里曾经是方圆百里最美的河流。按照上帝的旁白(是的,上帝担当旁白,上帝还是女的),污染是在1936年接了瘟疫的班,而“瘟疫那个老家伙退休时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青霉素”。长江后浪推前浪,汽车内燃机、塑料制品和高科技除草剂,这些都是污染的杰作,杀人不逊于战争和饥荒。
最后出场的是死神,是四骑士中的老大,只有他从未改变,也从未离开。普拉切特笔下的死神,就算是恶魔,也是睿智而幽默的,就像他“安慰”那个可怜的快递员,“不要把它想成死亡,就当是提前避开交通拥堵吧”。
最讽刺的是,无论天堂还是地狱,谁也不知道是谁召唤了四位末日骑士,也没有人知道,到底是谁打造了那些信物(炎剑、王冠、天平),只知道这些任务被外包给了国际快递公司。
就毁灭世界的重任而言,四位骑士只是配角,真正的主角是那个叫亚当的男孩,他是撒旦之子,承担着毁灭世界的重任,但却最终拯救了世界。当然,他也差点毁掉了世界,但不是因为他邪恶,而是因为他看到这个世界已经烂透了,不如干脆推倒重来。“你从小到大读到的都是海盗、牛仔、太空人,你刚觉得世上充满了这些神奇的东西,结果他们告诉你其实只有死鲸鱼和被砍掉的雨林和数百万年都不消解的核废料。要我说的话,这些东西真不值得让人长大。”
尼尔·盖曼在写给孩子的书里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成年人都不大靠得住。这就是为什么他的童书绘本很少引进过中国。我读过他的唯一一本绘本是《那天,我拿爸爸换了两条金鱼》,讲一个对孩子不管不问、只会埋头看报纸的爸爸,先被儿子拿来换了两条金鱼,但因为太无聊,又被转手换成吉他,又从吉他换成大猩猩面具,又从大猩猩面具换成兔子……最后儿子来找他时,发现他坐在兔笼子里,还在一边啃萝卜一边看报纸。
按照盖曼的说法,就像成年人都不大靠得住,西方一些自大的掌权者也一样,因为他们不具备自我怀疑的能力,他们从不觉得自己可能是错的,也很少把世界放在个人的目标前面。就像大天使加百列,他对天堂的绝对正确和必胜无疑抱着如此坚定的信念,有时候你忍不住想要冲着他那张自以为是的脸来上一拳。当然,更让人抓狂的是,上帝的“不可言喻”——“上帝从不跟宇宙万物玩骰子,他玩的是一种自己设计的不可言喻的游戏。从其他玩家(比如所有人)的角度类比来看,就像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房间里,用空白纸牌,以一切为赌注,玩一种复杂繁琐的纸牌游戏。庄家不但没告诉你规则,脸上还总挂着微笑。”
从这个角度看,《好兆头》这一出末日喜剧,看起来更像是政治讽刺剧,而不是奇幻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