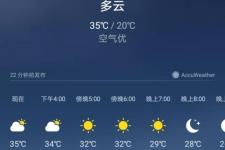我喜欢在夏天的夜晚出去看石头生长。沙漠上温暖干燥,我觉得它们在这里比在别处长得更好。也或许,活动的只是那些年轻的石头。
年轻的石头总是比长辈们认为适宜的要活动更多。大部分年轻石头都有一个秘密的愿望,它们的父母从前也有过但早已遗忘。而且因为这个愿望涉及水,所以从不被提及。老石头不赞成水,它们说:“水就像牛虻一样讨厌,从不肯在一个地方老实呆着学点儿什么。”然而年轻石头努力挪动,慢慢地,不被长辈发现,夏夜暴雨产生的激流可能会把它们冲到边上或未知地带,比如说把它们冲下山坡,冲进一个河谷。尽管这有点危险,但它们想要旅行,想看看世界并在新的地方安家,远离原来的家和父母的控制。
尽管石头家族的纽带非常牢固,一些勇敢的石头还是成功了,它们用身上的伤疤向自己的孩子证明,它们也曾去外面闯荡过,也曾旅行了十五英尺,一段难以置信的距离。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们便不再夸耀这类冒险行为。
的确老石头们变得相当保守。它们认为一切行动既危险又罪恶。它们在原地舒适地呆着,变胖。肥胖,事实上,是杰出的标志。
夏天的夜晚,当年轻石头入睡之后,年长的石头们会转向一个严肃而可怕的话题——月亮,总是被悄悄谈起。“瞧它发着光在天空移动,总是在变形。”一个说。另一个说:“感觉到吸力了吗,它在迫使我们跟随。”第三个低声说:“那是一块发疯的石头。”
Richard Shelton《The Stones》(三书 译)
青石白莲寄友人
/ /
《莲石》
(唐)白居易
青石一两片,白莲三四枝。
寄将东洛去,心与物相随。
石倚风前树,莲栽月下池。
遥知安置处,预想发荣时。
领郡来何远,还乡去已迟。
莫言千里别,岁晚有心期。
/ /
时见小孩子手里握着一块石头,或握着几片落叶,被妈妈牵着走在繁华的商业街上,他们并不看那些橱窗,而是专心玩自己拾到的宝贝。在小孩子眼里,比起名表和钻石,石头和落叶才是奇迹。
我也喜欢捡石头,看书的时候,手里经常握着一块青石:形如鹅卵, 石上绕有两道白纹,一粗一细,一深一浅,青石透着云样的黄褐色,石身遍布流水的纹理,也许是风留下的足迹。把它握在手中,就像握着一部神秘的地球简史。我对它一无所知,只知这是朋友从埃及的沙漠里捡来的石头。
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块石头。不必黄山奇石,不必苏轼的“雪浪”,随手在河边、在山谷捡一块石头,拿回来放在家里,也添得不少山水气象。
古代藏石赏石风靡士林,爱石成癖,为石写诗最多的,也许当数唐代诗人白居易。比如《双石》《太湖石》《青石》等诗,洋洋洒洒,对着一块石头,似乎有说不完的话。石头之可爱,之美德,正在于沉默吧,你尽管说,石头安静着,坦率的目光令你忽然感到赤裸。
莲石,这两个字放在一起,即是莲和石两样事物并置。自然万物,彼此间有着天然的默契,比如在盆栽植物旁边放一块石头,看上去就很舒服,如果放一个塑料袋或手机,感觉就不协调。石和莲,把它们连在一起的是水。
乐天给朋友寄去“青石一两片,白莲三四枝”,收到这份礼物该有多惊喜,何况还附了一首诗。他的心也随之到了东洛,并遥想朋友将如何安置莲石,“石倚风前树,莲栽月下池”。待到白莲花开,邻郡不远,不知我能否归来?
青石白莲,皆出尘之物,洁净清冷,乐天或借以寓意“岁晚有心期”,到时还乡,与朋友在东洛共度晚年,安贫乐道,自在逍遥。

清 朱耷《石头桐子图》
望夫处,江悠悠
/ /
《望夫石》
(唐)王建
望夫处,江悠悠。
化为石,不回头。
山头日日风复雨,
行人归来石应语。
/ /
人有没有可能化为石?对于超出经验和认知范围的事,我们如果不能证明,至少应保留其可能性。计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回答“不知道”,远比回答“不可能”,更有智慧,因为向未知敞开,就意味着将会有更多的发现。
石生人、人化为石的神话学背景可以追溯至远古时期。原始初民相信大石通灵,具有生殖能力,据《淮南子·修务篇》记载,大禹之母狄得石如珠,吞之生禹,大禹的儿子启,就是涂山氏至嵩高山下化而为石,从石中生出了启。在中原神话中,蚕神嫘祖死后化为奶头山,相传其山颇灵验,后世人常敲山前一块大青石许愿。
望夫石的故事在民间流传极广,各地多有,版本不一,情节大同小异,都是夫去不归妇人伫望日久化为山石。安徽涂山,武昌北山,桂林漓江,广东清远,香港沙田,都有“望夫石”,前二者在上古典籍中已有记载,后三者系石形似妇人,有的似还背着孩子,因此当地便幻想出类似的故事。究竟是否系人所化,我们不得而知,毕竟有较多文字记录的历史也才不到三千年(史书的信念系统未必可靠),而涂山氏如果真的化为石,那也已经四千多年了。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我等此生不足百年,又如何能知?漓江两岸姿态奇异的山峰,谁敢肯定它们不是由一群史前巨兽化成?也许它们被施了魔法,也许其中有些只是入定,也许哪一天就会醒来。
古代很多诗人都写过《望夫石》,写的都是石头的相思,其中王建的诗最为质朴平实,然而又能曲尽人意。“望夫处,江悠悠”,一启始便使人愁,亦景亦情,江水悠悠流不断,一日千年。
刘禹锡的《望夫石》曰:“终日望夫夫不归,化为孤石苦相思。望来已是几千载,只似当时初望时。”前三句铺叙,都是散文,唯有最后一句是诗,即化为石的那一刻,时间停止,定格在初望时。
王建的这首,句句是诗,每个句子都能唤起我们的内在感知,最后一句尤为点睛之笔。“行人归来石应语”,石不是石,当行人归来,到那时候,石就会开口说话。

清 朱耷《鱼石图卷》(部分)
无才可去补苍天
/ /
《题自画石》
(清)曹雪芹
爱此一拳石,玲珑出自然。
溯源应太古,堕世又何年?
有志归完璞,无才去补天。
不求邀众赏,潇洒做顽仙。
/ /
好小说都是好神话。纳博科夫的这句话,可以用作对《红楼梦》的评价。曹雪芹在小说的第一回叙述创作缘起,开篇就引入女娲补天的神话。女娲氏炼石补天,炼成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补天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单单剩下一块未用,弃在青埂峰下,此石自经锻炼,灵性已通,遇一僧一道,从而幻形入世,是为宝玉。从寓言角度来看,《红楼梦》的故事框架是顽石历劫,所以也叫《石头记》,借石头作为叙事者,不仅富有超现实色彩,更具多义隐喻的性质。
灵石崇拜普遍存在于古代不同民族的文化信仰中,古人将石头看作力量、生命、永恒和信义的象征。不仅《红楼梦》以灵石为叙事者,《西游记》里的主角孙悟空亦是东海神州花果山上一仙石孕育而成,而《水浒传》的第一回便出现一块青石板,所镇的就是龙虎山下一百零八个魔君,即后来的一百零八位梁山好汉。
曹雪芹故意将自己的作者身份隐去,而请石头作为叙事者,又让其幻形入世化为故事的主人公,聪慧的读者都能明白,灵石、宝玉、作者,实为一体。上面这首《题自画石》便可明示,曹雪芹画了一块石头,等同于他的精神写照,并为其题诗。
爱石自不必说,对着石头,他自然想到太古。“溯源应太古,堕世又何年?”大概自有天地,便有此石,堕世就是来到人间,不知是何年月。“有志归完璞,无才去补天。不求邀众赏,潇洒做顽仙。”这四句不是写石,是以石自喻,写他自己了。无才去补天,不是忏悔语,实乃愤激之辞,此天不是苍天,也不是封建社会所谓的“天”,而是民族生命力延续之“天”。
《红楼梦》第一回的石上偈曰:“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记去作奇传?”不论此偈,还是题画诗,都能看出曹雪芹精神上的失落。而从他对社会问题的揭示,以及对生命自由的书写来看,小说其实已具有了“补天”的意义。
想想我手中这块青石,在我之前,不知它经历过什么,到过哪些地方,我又将携它前往何方,如果丢掉,它会被谁拾起,或在某个角落呆着,不管怎样,我们终将分离,各归各的去处。
石能否化为人,人能否化为石?想象这些可能,远比草率回答更为重要。想象力就是创造力,如果诸相非相,万法皆幻,那么想象在本质上就等同于现实。维特根斯坦在《最后的哲学笔记》中写道:“没有相信奇迹的能力,不在于一个人不相信离奇之事,而在于他无法从中看到多于离奇之事的东西。相信奇迹的人则将离奇之事视作破入另一世界的门径,视作更高存在者的探言。”
作者/三书
编辑/张进 何安安
校对/